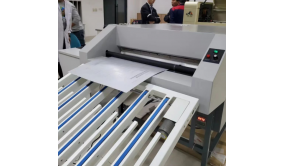对美国人的电视经验来说,他不需要出去看任何特别要看的东西:他只要转动一下旋钮,然后边看边琢磨就是了。这个节目是现场直播还是播放录像?这只是在放动画片还是在模拟什么?这是再度上映的电视片吧?它取材于何处?这种事情如果真的发生过,那么它确实发生在何时?那是演员在演戏还是真人真事?那是电视商业广告吧?——是商业广告的骗人把戏?——纪录影片?——还是纯粹虚构的故事?看电视的人几乎从来不是从纯粹个人的角度来看电视上的事情的。
因为电视是从多方面着眼的,时刻注意避免根据任何一个人的有限视野把画面弄得单调乏味。只要摄影机把图像拍得比实物更大、更清楚,没有人会阻止它那样做。随着特写镜头充斥电视屏幕,中距离镜头也就消失了。在客厅里看电视的人看到棒球手在左翼外场,击球手在本垒,或者吵吵嚷嚷的观众在露天看台上,这些他比看台上那个戴太阳眼镜的人看得还要清楚。任何临时出现的傻瓜,或者匆匆露面的名人,都会塞满电视屏幕,就像汉弗莱·博加特或者尼克松总统那样。全部电视经验变成了剧院,任何演员,或者甚至一个观众,都可能占据舞台的中心。
对比之下,电视的这种前所未有的效果,使美国人理所当然地不愿再回到他的边座或后座上去。当整个世界成了电视的舞台的时候,莎士比亚的比喻也就成了无情的现实。在这个代理经验的超级市场上,旧有的分隔不见了。去教堂或去听课和去看戏或看电影或看球赛没有任何区别,与参加政治集会或停下来听成药推销员的推销宣传也没有任何区别。几乎任何东西你都可以身着衬衣、手拿啤酒罐头来观看。通过电视渠道流出来的经验,有娱乐,有教育,有新闻,有道德鼓吹,有规劝,还有你猜是什么吧。
编排得成功的节目提供娱乐(打着教育的幌子)、教育(打着娱乐的幌子)、政治主张(具有广告宣传的号召力)和广告宣传(具有戏剧的魅力)。这种新的瘴气不是过去的任何机器所能产生的,它笼罩了电视世界,进而使“真实的”世界蒙上一层迷雾。美国人开始时对这种迷雾见怪不怪,对眼前的一片混沌安之若素,并引以为乐,结果,现实本身由于其轮廓清楚,由于其人物、地点、时间和境遇历历分明,反而有点令人不快了。
电视广播技术的进步,往往又使看电视的人的经验变得更加间接,更加为看不见的节目制作人和技术人员所控制。过去,全国政治大会上的观众只要转动脑袋,就可自己决定往哪里看,但现在在客厅里看电视的人却没有这种决定能力。摄影师、导演和评论员替他决定了,一会儿让他看一个凶暴的警察,一会儿又让他看一个手腕巧妙的代表。由于这些政治大会由电视摄影机来导游,评论员本身也获得了一种影响公民政治经验的新的本领,这种本领在1968年在芝加哥召开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得到了最生动的表现。
甚至在美国人的第二手经验终于变得似乎更真实、更可靠的时候,它也比以往更加受那些抢主要演员的镜头而大出风头的无形的手和导游人的影响。人们看电视成了瘾,对电视的迷恋只有对生活本身的迷恋可以与之相比。如果电视机没有打开,美国人就开始觉得错过了机会,没有看到“真的在发生”的东西,正如活总比死好是不证自明的道理一样,看些什么比什么都不看好这个道理也是不证自明的。如果“今晚电视没有什么节目”,那么人们就会产生一种痛苦的空虚之感。这就无怪美国人要修正他们判断经验的标准了。即使那些不值得有的第一手经验,放到电视上去也许就值得有了。
在关于电视的种种奇迹中,再没有什么比电视出现的速度更值得注意的了。电视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内征服了美国,使全国处于迷惘的状态之中而不敢承认。印刷机使知识民主化花了五百年时间。当人民能够和他们的“长官”知道得一样多的时候,他们就要求得到自治的权力。迟至1671年,弗吉尼亚总督威廉·伯克利爵士还在为印刷机(异端邪说和犯上作乱的罪魁祸首)不曾来到他的殖民地而感谢上帝,他衷心祷告,但愿印刷术永远不会来到弗吉尼亚。到了十九世纪初,一些贵族和文人,包括托马斯·卡莱尔在内,都能记下这样的情况:活字解散了雇用的军队,废黜了国王,并以某种方式创造了“整个民主的新世界”。
现在,电视以令人头晕目眩的速度把经验民主化了。电视和它以前的印刷机一样,受到了知识分子、学究先生以及传统经验途径的所有其他卫道士的冷遇,这也就没有什么奇怪了。“现在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政府机密泄露给报界?”《纽约时报》的见多识广的詹姆斯·赖斯顿在1972年1月提出了这个问题。自从关于越南战争的成篇累牍的背景材料——五角大楼文件未经授权地公布以来,这个问题一直使全国感到苦恼。但赖斯顿对这个问题的解释既不是政治上的,也不是哲学上的,更不是道德上的,而纯粹是科学技术上的。
他提出:“泄露机密的真正罪魁祸首是切斯特·卡尔森,因为是他发明了静电复印(亦称施乐影印法),而这种影印法联邦政府内到处使用,并影响着全国其他每一个大机构的情报往来。”有了施乐影印机,任何人都能立即把任何文件复制出来。发明这种机器的本来目的是“扩大知识和真理”,而根据赖斯顿的说法,这种机器却产生了令人啼笑皆非的结果,使政府官员在书面表达他们的真正观点时小心翼翼。
就种种实际效果来看,已不能够再肯定地说哪一份文件是独一无二的了。照片凸版印刷和其类似技术,曾经使珍贵的文学手稿和初版图书失去其作为海内孤本的价值。到1965年,照相凸版复印的莎士比亚的第一个对开本(原版每本售价三万美元)只用十五美元就可买到一本。复印整本书或书中的某些部分非常容易,也非常便宜,以致版权法正在成为过时的东西。
施乐和其他静电复印法扩大了经验的可再现性的范围,只要弄到一部简单的机器,谁都能破坏任何文件的独一无二性和机密性。现在,北极星照相机、磁带录音机、录音磁带、录像磁带和其他手段也同样提供了可以立即重放的复制品,把日常生活变成了许许多多成批生产出来的瞬间。现在,任何人看到的或听到的几乎任何东西,无数身份不明的人也同样能够看到或听到。
制造一式多份的复本这个问题和文字一样古老。当然印刷机和活字版的出现,使知识民主化了。但是,除非能制造出许多复本来,否则排字的费用就不合算,而制造出来的复本越多,每一个复本的成本就越低;如果需要的复本达到成千上万,那么印刷机明显地就发挥了最大的效益。正如爱迪生在使电灯民主化时碰到的问题是如何把光分成更小的光源一样,在复制技术中也存在类似问题。在印刷机普遍使用后的几百年中,由于没有任何其他办法制造出单独的复本,“抄写员”的职业得以维持下来,这些人的工作就是用手抄办法来复制原件。
灵巧的“复写器”是十八世纪的发明,它把一种装置同书写人的笔连在一起,把字的一笔一划在另一张纸上再现出来,就这样一边写信,一边复制。托马斯·杰斐逊对这种机器大感兴趣,并对其作了一些改进。但是,制造一个单独复本的常用方法,仍是使用书信复写器:信写好后,把它夹在吸墨纸中滚压,使一些墨迹印到另一张纸上。在杰斐逊时代,人们还不知复写纸为何物,但在后来它却成了一种极大的方便,因为它不需要任何机械装置,它价格便宜,并能在产生原件的同时产生复本。
使少量制造清楚可读的复本一事变得更加容易的机器,当然要算打字机了。甚至在十九世纪以前,英国的一些发明家就已在发明一种书写机器方面取得了某些进展。到1845年,也就是在可供实用的手操作打字机出现之前二十年,塞缪尔·F·B·莫尔斯和他的合伙人用一种很像打字机键盘的东西,通过电磁长距离地输送机器书写。C·莱瑟姆·肖尔斯是威斯康星的一个富于首创精神的人,他在密尔沃基当印刷工兼编辑,用以谋生,并一直在研究一种自动号码机,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朋友建议他发明一种字母打印机。
 客服热线:
客服热线: